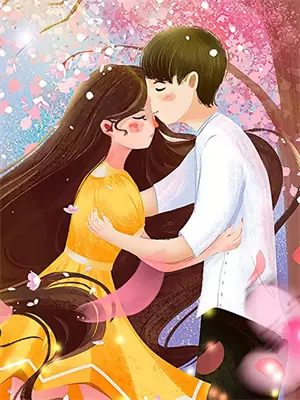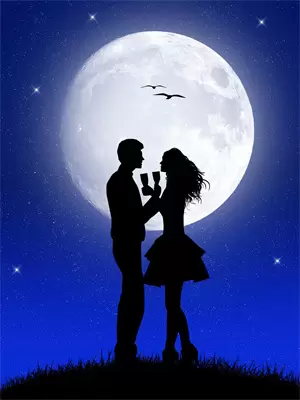第一章虫洞指尖触碰到那柔软的金箔时,林晚总会不自觉地屏住呼吸。
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室,时间在这里仿佛被刻意拉长、凝滞,
最终沉淀在纸张、墨香和一丝若有若无的霉味里。午后阳光透过高大的玻璃窗,
被分割成一道道澄澈的光柱,无数微尘在光中无声飞舞,像一场永不停歇的寂静芭蕾。
她伏在宽大的红榉木大案前,案上铺着一本清代的《民间织造图谱》。书页脆弱得如同蝶翼,
边缘是虫蛀留下的、密密麻麻的孔洞,仿佛岁月的疤痕。她的工作,
就是用比头发丝还细的钢针,蘸取特制的浆糊,
将薄如蝉翼的金箔小心翼翼地补在那些蛀洞上。这是一种以金续命的医术,
对象是这些行将就木的故纸。周围极其安静,只有空调系统维持恒温恒湿的微弱嗡鸣,
以及自己清浅的呼吸声。这种静,是她习惯并依赖的铠甲,
将她与外面那个过于喧嚣的世界隔绝开来。父母早逝带来的那种深入骨髓的、对失去
的恐惧,唯有在这片静止的时空里,才能得到片刻的安抚。今天要修补的这一页,
绘着一幅繁复的并蒂莲纹样。一个不起眼的虫蛀,恰好落在莲花的花蕊处。
林晚用镊子夹起一片裁切好的菱形金箔,在放大镜下,精准地置于蛀洞上,
然后用裹着丝绸的玛瑙轧子,轻轻地、均匀地碾压。金箔完美地贴合,填补了时间的空缺,
在光下泛着温润内敛的光泽。就在这时,异变发生了。就在刚刚补好的金箔旁边,
那片原本空无一字的纸页上,毫无征兆地,浮现出了一行墨字。字迹是新鲜湿润的,
仿佛刚刚写就,甚至还反射着一点窗外的光。那是一种瘦硬清峻的钢笔字,
带着民国时期特有的文人风骨。林晚的动作瞬间僵住,浑身的血液似乎都冲向了头顶,
耳边一片轰鸣。她死死盯着那行字,内容更是让她毛骨悚然:今日金箔成色比昨日好,
像你耳尖的颜色。……像你耳尖的颜色?林晚猛地抬起头,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。
修复室里空无一人!同事们都已下班,厚重的实木大门紧闭着,
只有一排排修复到一半的古籍,在巨大的书架上沉默地矗立,像一片沉默的墓碑。谁?
是谁在恶作剧?她几乎是条件反射地环顾四周,视线扫过每一个可能藏人的角落。没有人。
甚至连一丝风都没有。这里的安保级别极高,进出都需要权限,绝无可能有外人潜入。
是幻觉?过度疲劳导致的?她用力闭上眼睛,深吸了几口气,
那混合着纸张、浆糊和淡淡樟木香气的空气涌入肺腑,让她稍微冷静了些。然后,
她再次睁开眼,看向那页纸。字,还在。墨迹甚至看起来比刚才更清晰了一些。
那耳尖的颜色几个字,像带着温度,让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耳垂。
刚才全神贯注工作时,这里确实因为微微充血而有些发烫……一股寒意从脊椎骨窜上来,
让她打了个冷颤。她强迫自己移开视线,放下手中的工具,起身去倒了一杯水。
冰凉的水滑过喉咙,却无法浇灭心头那股诡异的火焰。她回到案前,
目光不受控制地再次落在那行字上。它就在那里,坦然、安静,
却充满了打败一切常理的力量。这不是恶作剧。恶作剧无法解释这墨迹是如何凭空
出现在一本清代古籍的内页上的,也无法解释那精准的、关于她此刻身体细微变化的描述。
她盯着那墨迹,一个荒谬绝伦的念头浮现在脑海。
她重新拿起一支用于标记的、极细的绘图铅笔,指尖微微颤抖着,在那行字的下面,
小心翼翼地写下:你是谁?写完这三个字,她立刻将笔丢开,仿佛那笔杆烫手。
她紧紧盯着书页,心脏提到了嗓子眼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。什么也没有发生。
窗外的天色渐渐暗淡,夕阳的余晖给房间镀上了一层暖橙色的边。那页纸安静如初,
她写下的铅笔字,和那行诡异的墨字并排躺着,像是分属两个毫不相干的世界。
自嘲地笑了笑。果然是太累了吧。或许该去找心理医生聊聊了。她站起身,开始收拾工具,
准备结束今天的工作。就在她将轧子放回工具盒,发出清脆的碰撞声时,
眼角的余光似乎捕捉到了什么。她猛地转头。书页上,就在她铅笔写下的你是谁?
的正下方,一行新的墨字,正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,从容不迫地浮现出来!
仿佛是有一支看不见的钢笔,正在从容不迫地蘸墨、书写。笔画清晰,结构舒展。
林晚屏住呼吸,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,一动不敢动,
眼睁睁看着那行字完整地呈现:一个读者。恐惧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,
却又奇异地混合进了一种难以言喻的、近乎疯狂的兴奋。她不是疯了。有什么东西,
真的发生了!某种超越了物理规则的联系,建立了!她几乎是扑回到案前,再次抓起铅笔,
因为激动,字迹有些潦草:你在哪里?你怎么能看到我?怎么听到我的?这一次,
她没有等待太久。在她落笔后不过十几秒,新的批注便出现了,
字迹依旧从容不迫:我在看书。至于如何看到、听到……恕我暂不能言明。惊扰之处,
还请见谅。只是姑娘修复技艺精湛,心无旁骛,令人心折。他的用词文雅而克制,
带着一种旧时代特有的礼貌。这种礼貌,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林晚最初的惊骇。
她慢慢坐回椅子,目光在那几行跨越了某种界限的对话上来回扫视。一个能看到她、听到她,
却无法直接沟通的……读者?他在读什么书?难道他读的,
就是她手中正在修复的这本《民间织造图谱》?可这怎么可能?无数的疑问在脑中盘旋。
但她知道,此刻追问根源恐怕得不到答案。她换了一个问题,
用铅笔写道:你看的是这本《民间织造图谱》?是。此乃孤本,损毁可惜。
幸得姑娘妙手回春。他果然在看这本书!林晚感到一阵眩晕。这意味着,
他们不仅跨越了空间,很可能……也跨越了时间?一个穿着民国长衫的文人形象,
不由自主地在她脑海中勾勒出来。这个念头让她口干舌燥。她犹豫了一下,
写下:现在是哪一年?问题发出后,那边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
书页上久久没有新的字迹出现。就在林晚以为触犯了什么禁忌,或者联系已经中断时,
墨迹终于缓缓浮现:民国十六年,西元一九二七年。一九二七!尽管已有预感,
但当这个年份真切地出现在眼前时,林晚还是感到一阵巨大的冲击。近一百年!他们之间,
隔了将近一百年的时光!她怔怔地看着那个数字,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。
修复室的灯光已经自动亮起,在明亮的白光下,那几行墨字显得更加突兀和不真实。
民国十六年……她无意识地低声重复了一遍。几乎是她话音落下的瞬间,
书页上立刻出现了新的批注:你的声音,很好听。林晚猛地捂住嘴。他听到了!
他不仅能看到她的工作,还能听到她无意间的低语!这种无所遁形的感觉让她再次紧张起来,
但这一次,紧张中掺杂了一丝微妙的心悸。在一个世纪前的某个人,正在聆听她此刻的声音。
这种联系,诡异、危险,却又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、宿命般的亲密感。她稳定了一下心神,
决定不再追问那些暂时无法理解的问题。既然联系建立了,她需要了解更多关于他
的信息。她拿起铅笔:你叫什么名字?沈砚。砚台的砚。沈砚。
她在心底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。很配他那手清峻的字。林晚。晚上的晚。
她写下自己的名字,作为一种平等的交换。林晚……墨迹勾勒出她的名字,
仿佛带着一丝沉吟的意味。好名字。夜阑人静,宜读书,宜会友。他称此为会友。
林晚的嘴角不自觉地微微牵动了一下。与一个近百年前的陌生人,通过书页批注会友,
这实在是她二十多年人生中,最离奇,也最……浪漫的遭遇。接下来的时间,
他们开始了这种极其特殊的交谈。大部分是林晚用铅笔问,沈砚用钢笔答。他告诉她,
他是北平图书馆的管理员,负责古籍的整理与编目。
这本《民间织造图谱》正是他经手过的书籍之一,见到它被如此精心修复,他深感欣慰。
他的言辞始终保持着得体的距离,却又在细节处流露出敏锐的观察力。
他会评论她使用浆糊的浓稠度是否恰到好处,会在她成功修复一处特别复杂的破损时,
批注一句妙极。这种被一双来自过去的眼睛默默注视的感觉,起初让林晚如坐针毡,
但渐渐地,一种奇异的安心感取代了不安。在这个寂静的、常常只剩下她一个人的修复室里,
她第一次感到,自己并非完全独处。时间在无声的笔谈中流逝。直到窗外夜幕深垂,
城市华灯初上,林晚才惊觉已过了下班时间许久。她写下:很晚了,我该走了。
沈砚的回复很快:路上小心。明日……再见。再见两个字,让林晚心头微微一动。
她收拾好东西,将《民间织造图谱》小心地放入专用的书函中。在离开修复室前,
她鬼使神差地走到墙边,那里挂着一幅图书馆老馆的黑白照片,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。
她看着照片上那栋庄严的建筑,试图想象沈砚穿着长衫,穿行于其间书架的身影。
民国十六年,一九二七……那似乎并不是一个太平的年月。带着满脑子的纷乱思绪,
她回到了位于图书馆附近的老式公寓。房间不大,但布置得温馨,承载着她许多回忆。
她习惯性地走到玄关的五斗柜前,那里摆着几张照片。最中央的,
是她童年时唯一一张与父母的合影。照片上的她大约三四岁,被父母簇拥在中间,
笑得没心没肺。然而,就在她的目光落在相框上时,她的动作顿住了。
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协调感涌上心头。她疑惑地拿起那个木质相框,仔细端详。照片完好,
父母和她笑容依旧。
但是……她用手指轻轻抚摸相框的金属扣环——那是用来打开相框更换照片的活扣。
扣环还在,但是……它看起来光秃秃的。记忆中,这个金属扣环的顶端,
似乎应该镶嵌着一小颗……什么东西?是仿制的绿松石?还是红色的塑料点缀?她努力回想,
却发现关于这个细节的记忆异常模糊,就像隔着一层毛玻璃。她明明记得应该有个装饰物的,
小时候她还经常用手去抠弄它。可现在,扣环就是一个光滑的、毫无特色的金属扣。
是时间太久,脱落了吗?还是自己记错了?她蹙着眉,
试图在脑海中勾勒出那个装饰物的清晰模样,却无论如何也抓不住。
一种微妙的、怅然若失的感觉萦绕在心头,虽然轻微,却无法忽略。最终,
她只能将相框放回原处,将其归咎于自己最近精神压力太大,记忆出现了偏差。毕竟,
今天经历了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,大脑有些混乱也是正常的。她没有将这个小小的插曲,
与几个小时前在那本清代古籍上开始的、那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联系起来。窗外,
城市的灯火无声流淌。而在书房的案头,那本合上的《民间织造图谱》内页里,属于沈砚
的墨迹早已干透,静静地等待着下一个明天的开启。只有窗外清冷的月光,
映照着玄关那张照片上空空如也的金属扣环,闪烁着一点微茫的、如同疑问般的光。
第二章崩塌法则接下来的几天,林晚的生活被割裂成两个泾渭分明又诡异交织的部分。白天,
她在修复室里与其他同事一样,进行着按部就班的修复工作,
讨论着浆糊的黏度、纸张的酸碱度。但每当她独自一人,
或是午休、下班后留在修复室的片刻,她就会迫不及待地打开那本《民间织造图谱》。
与沈砚的笔谈,成了她日复一日静谧生活中,一道隐秘而炽热的裂隙。他们交谈的内容,
从最初的试探,逐渐变得广泛而深入。沈砚的博学与睿智,透过那瘦硬清峻的字迹,
缓缓流淌过来。他能精准地点评她修复手法的精妙之处,
也能信手拈来地讲述某一种织物纹样背后所承载的民俗与历史。他的言辞,
总带着一种旧式文人特有的温润与克制,但偶尔,也会流露出超越时代的、对时局的忧思。
近日局势颇不太平,他曾在一处批注里写道,墨迹似乎比平时更深沉,
馆内同仁皆忧心典籍之安危。若战火燃及,这些故纸,不知将流落何方。
林晚看着这行字,心头沉重。她知道一九二七年意味着什么,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夜。
她想告诉他未来会发生什么,想警告他,但铅笔提起,又落下。
一种无形的约束感让她无法落笔,仿佛一旦泄露天机,这脆弱的联系便会瞬间崩断。
她只能写下苍白的安慰:会好起来的,总会有人守护它们。沈砚的回复很快,
带着一丝苦涩的自嘲:是,吾辈职责所在,当与典籍共存亡。共存亡三个字,
像冰锥一样刺了林晚一下。她不敢深想。除了这些略显沉重的话题,
更多的是一些琐碎而奇妙的分享。林晚会告诉他,窗外那棵老槐树开花了,香气能飘进室内。
第二天,沈砚便会批注:馆前亦有槐树数株,花香袭人,想来与姑娘所闻,
是同一缕风送来的。她偶尔抱怨北方的干燥让纸张容易发脆,
他则会分享他们那个时代用宣纸包裹、放入樟木箱防潮的土法子。
这种跨越时空的、细节上的呼应,产生了一种极其玄妙的亲近感。林晚开始习惯在工作时,
低声自语,仿佛在向一个看不见的同伴倾诉。而沈砚,也总能适时地给予回应,
或是解答她的专业困惑,或仅仅一句辛苦了。
她甚至开始期待他那偶尔流露的、带着分寸感的关切。比如她某天咳嗽了两声,
批注便会提醒:春寒料峭,望珍重。她熬夜修复时,他会写:子时已过,歇息片刻吧。
这种被默默注视和关怀的感觉,像一缕温煦的光,
照进了她因孤独和过往阴影而显得有些清冷的心房。那本《民间织造图谱》,
不再是冰冷的修复对象,而成了连接两个灵魂的、温暖的桥梁。然而,这种日渐生长的暖意,
很快被一股彻骨的寒意打断。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,修复室里只剩下林晚一人。
她正在修复图谱中描绘云锦织造工艺的一页,难度极大,精神高度集中。或许是太累了,
她无意识地哼起了一段旋律,一段模糊的、盘旋在她记忆深处的童谣调子,
连歌词都记不清了。哼完,她并未在意,继续专注于手中的金箔。过了一会儿,
她习惯性地看向书页,期待沈砚或许会对云锦发表些见解。批注果然在那里,
内容却让她微微一怔:方才所哼之曲,调甚悲凉,可是《苏武牧羊》?林晚愣住了。
苏武牧羊?她从未听过这首歌,更不可能哼出来。她努力回想自己刚才哼了什么,
却发现那段短暂的旋律像泥鳅一样从记忆里溜走了,只留下一点模糊的、带着伤感的余韵。
她摇摇头,写下:不是,可能只是随便哼的,记不清了。沈砚没有继续追问。
这件小事像一粒小小的尘埃,并未在她心中留下太多痕迹。直到她下班回家,
习惯性地去抚摸那张全家福相框。手指触碰到冰凉的金属扣环,那种空落落的感觉再次袭来。
而且,这一次她清晰地感觉到,扣环旁边,相框木质边缘的一小块区域,
原本似乎应该有一处细微的、被什么东西反复摩挲留下的光滑凹痕?现在,
那片区域摸起来和其他地方一样粗糙。记忆再次变得暧昧不清。
她甚至不确定那凹痕是否真的存在过。一种难以言喻的不安,像阴湿的苔藓,
悄悄在她心底滋生。真正的转折点,发生在三天后。那晚,她因为要赶一个修复进度,
在修复室待到很晚。窗外下起了淅淅沥沥的春雨,雨声敲打着玻璃,更显得室内空旷寂静。
为了驱散雨夜的清冷,她打开了手机,播放了一首舒缓的钢琴曲,轻柔的音乐在空气中流淌。
她一边工作,一边和沈砚笔谈。许是雨夜容易让人感怀,
沈砚的批注也带上了一丝罕见的、个人化的情绪。今夜亦雨。忆起昔年在沪上,
曾于友人处听得一曲《夜来香》,歌声婉转,伴以留声机沙沙声,至今难忘。
林晚看着这行字,脑海中几乎能想象出那个画面:昏黄的灯光,老旧的留声机,
旋转的黑胶唱片,慵懒缠绵的歌声飘荡在雨夜的空气中。那种旧时代的、慢节奏的浪漫,
让她心向往之。她下意识地环顾了一下修复室,目光落在墙角一个蒙着防尘布的高大家具上。
那是图书馆早年收藏的一台老式手摇留声机,铜质大喇叭,桃木机身,
作为历史文物存放在这里,早已不能使用,更像是一个时代的装饰品。她心血来潮,
写下:真巧,我们这里也有一台老留声机,和你描述的那种很像,就放在墙角。
沈砚的批注带着明显的兴致:哦?亦是手摇式,铜喇叭否?若有机缘,
真想再听一回那靡靡之音。靡靡之音四个字,让林晚不禁莞尔。
她回复:可惜是文物,不能启动了。不然,真想放给你听。笔谈在雨声中继续。
直到深夜,林晚才完成工作,收拾好东西,关掉音乐和灯,离开了修复室。离开前,
她最后看了一眼墙角那台在阴影中沉默的留声机,防尘布勾勒出它优雅而孤独的轮廓。
第二天是周六,林晚下午才去图书馆。她需要查阅一些关于清代织造署的档案资料。
当她推开修复室的门时,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异样感扑面而来。室内一切如常,
阳光透过窗户,照亮空气中飞舞的微尘。同事们还没来,只有她一个人。她走向自己的座位,
目光习惯性地扫过墙角。然后,她的脚步钉在了原地,血液仿佛瞬间凝固。墙角,空了。
那块一直蒙着留声机的、米白色的防尘布,软塌塌地堆在地上,
仿佛一个被抽去了骨架的躯壳。而防尘布上面,空空如也。那台沉重、硕大的老式留声机,
不见了。林晚的大脑一片空白。她眨了眨眼,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房间。没有错,
这就是她的修复室,墙角的书架,窗边的绿植,一切都没变。唯独那台留声机,消失了。
她快步走过去,捡起那块防尘布。下面什么都没有,
只有积年累月留下的、一个清晰的留声机轮廓的印痕。地板上没有拖拽的痕迹,窗户紧闭,
门锁完好。怎么可能?一台那么大、那么重的文物留声机,怎么可能凭空消失?
一个荒谬而恐怖的念头,像毒蛇一样,骤然缠上了她的心脏。昨晚……她猛地回想起来。
昨晚,她和沈砚谈到了留声机!他提到了《夜来香》,
他表达了对留声机的怀念和想再听一次的愿望!然后……然后它就不见了!是巧合吗?
第一次,相框扣环上的装饰物,她可以归咎于记忆模糊。第二次,相框边缘可能存在的凹痕,
她可以认为是自己想多了。可这一次,是整整一台留声机!
一个无法忽略的、实体庞大的物件!它实实在在地从上了锁的房间里蒸发了!
冷汗瞬间浸湿了她的后背。她扶着墙壁,才勉强站稳。她跌跌撞撞地回到自己的座位,
颤抖着手打开书函,取出那本《民间织造图谱》。她几乎是粗暴地翻动着书页,
寻找沈砚的批注。找到了!昨晚关于留声机的那几段对话,墨迹清晰地印在那里。那不是梦,
不是幻觉!她用铅笔,用力地、几乎要划破纸页地写道:留声机!
墙角那台老留声机不见了!今天早上,它消失了!是不是……是不是因为我们昨晚提到了它?
她死死地盯着书页,心脏狂跳,几乎要冲破胸腔。时间在死寂中流逝,
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窗外的阳光明媚得刺眼,
与她内心的惊涛骇浪形成残酷的对比。终于,新的墨迹,
以一种极其缓慢、仿佛也带着难以置信的沉重速度,浮现出来:我……不知。但我方才,
在我这边的库房角落,看到了一台……此前并未留意过的留声机。样式……与姑娘所述,
一般无二。轰——!林晚的整个世界,在这一刻,仿佛被这道批注彻底击碎了。
猜想被证实了!不是巧合!不是她的记忆出了问题!他们之间的互动,
他们共同关注、尤其是沈砚强烈情感投射的物件,会从她的时空中消失,
并……出现在他那边!这意味着什么?这意味着他们这种跨越时间的联系,
正在以一种无法理解、无法控制的方式,侵蚀着她的现实!这一次是一台留声机,下一次呢?
会是什么?恐惧,巨大的、源于认知被打败的恐惧,像冰冷的潮水,瞬间将她淹没。
她之前所沉浸的那种隐秘的温暖和浪漫,在此刻显得如此可笑和危险。
她看着沈砚那行同样充满震惊与无措的字迹,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。
他们不是在玩一个有趣的游戏。他们可能……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。
第三章规则的阴影留声机的消失,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,
在林晚的世界里激起了永不宁息的涟漪。修复室那熟悉的恒温恒湿环境,
再也无法给她带来丝毫安全感。墙角那块空荡荡的地板,和软塌塌堆叠的防尘布,
成了她视野里无法忽视的、刺眼的空白,无声地宣告着现实的脆弱。
恐惧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而淡化,反而像渗入织物的墨迹,不断弥漫、深化。
她开始神经质地检查修复室里的每一件物品,确认它们是否还在原位。
对同事随口提起那台老留声机是不是搬去保养了?的疑问,她只能含糊地点头,
后背却惊出一身冷汗。她与沈砚的笔谈,气氛也陡然转变。
之前那种带着朦胧暖意的分享与探讨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凝重而急迫的求证。
林晚几乎是用颤抖的手,在《民间织造图谱》的空白处,
写下了一连串的问题: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为什么东西会消失?规律是什么?
我们这样对话,是不是在加剧这一切?沈砚的回应迟来了很久,墨迹显得异常沉滞,
仿佛书写者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:林晚姑娘,稍安。我亦百思不得其解。此事太过诡谲,
超乎你我认知。然恐慌于事无补,我们需得冷静,方能寻得端倪。他的冷静像是一盆冰水,
稍稍浇熄了林晚心头的慌乱之火,却也让她更深刻地意识到,
他们面对的是一种何等未知而强大的力量。如何冷静?她写道,笔尖带着一丝无力感,
下一次消失的会是什么?我的桌子?这整间屋子?还是……我本身?断不会至此!
沈砚的批注回复得极快,带着一种斩钉截铁的意味,我虽不明原理,但观此前迹象,
消失之物,似皆与我有关。他条分缕析地写下:其一,相框饰物,你言乃你珍视之物,
或与我未能护住某些……类似回忆有关?其二,留声机,是我明确提及、心向往之之物。
其共通点,在于『我』之执念或关联。林晚看着他的分析,心脏一点点沉下去。是的,
指向性太明显了。每一次互动,每一次情感的共鸣,尤其是来自沈砚那边的强烈情绪,
都像是一把无形的钥匙,开启了现实层面的交换或者说……掠夺。所以,
是因为你?因为你的念头,你的渴望,我这边的东西才会被夺走,送到你那里?
她写下这句话时,感到一阵尖锐的刺痛。这并非指责,
而是一种基于事实的、令人心寒的推论。沈砚那边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
那空白仿佛是有重量的,压得林晚喘不过气。她几乎能想象到,隔着近百年时光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