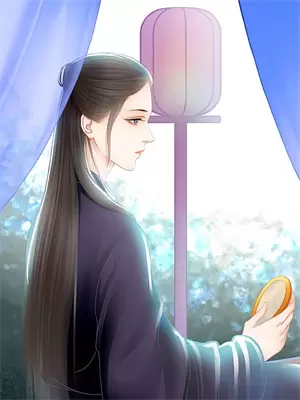我叫陈实,一个跑腿的。每天累得跟狗一样,最大的安慰就是住处有个热心肠的房东方姐。
她总会给我留一碗热汤,嘱咐我注意身体。直到我送了一单快递,成了杀人嫌疑犯。
死的是个网红,死在她自己的豪宅里,而我是最后一个见过她的人。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我,
监控视频更是铁证如山。就在我快被全世界抛弃的时候,只有方姐还信我。
可我的出租屋开始闹鬼。死去的网红总在深夜出现,卫生间的镜子上会浮现血字,
走廊里还有她的哭声。我以为是冤魂索命,直到我发现,每次“闹鬼”,
方姐都恰好出现来安慰我。我开始怀疑,这世上最可怕的,或许不是鬼。
而是那个每天对你嘘寒问暖,笑着递给你热汤的人。1我叫陈实,是个跑腿的。说白了,
就是个没坐骑的骑士,整天在城市里窜来窜去,送一切能送的东西。文件、鲜花、宵夜,
偶尔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委托。我住的地方,是个老破小,叫“安福里”。
楼道里贴满了开锁通厕的小广告,墙皮一碰就掉渣。我喜欢这儿,因为租金便宜。
还因为我有个好房东,方姐。方姐四十来岁,一个人住我对门,是这栋楼的二手房东。
人特别热心,见我一个小年轻天天跑得跟孙子似的,总照顾我。今天加班晚了,
她会端碗热汤过来。明天看我衣服破了,她能找出针线给我缝好。用她的话说:“小陈啊,
出门在外的,都不容易。”我挺感激她的。在这座几千万人的大城市里,这碗汤,
比什么都暖。今天这单,有点远,是个叫“江畔公馆”的地方。富人区。我骑着我的小电驴,
感觉自己像个闯入别人世界的蚂蚁。门口的保安拦下我,上下打量,那眼神,
像是在看一坨会移动的垃圾。登记、打电话确认,折腾了快十分钟才放行。客户叫于瑶,
是个网红。我给她送过几次东西,都是些奢侈品的盒子,或者从国外寄来的化妆品。
人长得跟照片里一样,就是脾气不太好。每次开门,脸上都挂着不耐烦,
好像我耽误了她几百万的生意。我按下门铃。没人应。又按了一次。还是没动静。
我掏出手机准备打电话,发现门虚掩着,留着一条缝。“于小姐?”我试探着喊了一声。
“快递放门口就行了!”屋里传来她的声音,带着一股子火气。我哦了一声,
把手里的盒子放在门口的地垫上。拍照,上传系统,完成订单。正准备走,
那门缝里飘出一股奇怪的味道。不是香水味,也不是饭菜味。
是那种……铁锈和什么东西腐烂混合在一起的腥气。我皱了下眉,没多想。有钱人的品味,
我搞不懂。我骑着小电驴往回赶,脑子里盘算着这个月还能剩多少钱。回到安福里,
天已经全黑了。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两个,一闪一闪的,跟恐怖片似的。我摸黑上了三楼,
掏钥匙开门。对门的方姐开了门,探出头来。她穿着件围裙,手里还拿着锅铲。“小陈,
回来啦?吃饭没?”“没呢,方姐。”我笑笑,露出一口白牙。“正好,我今天做了红烧肉,
给你盛一碗去。”她说着,转身进了厨房。我心里一暖。这就是我留在这个破地方的理由。
我打开门,一股泡面的味道扑面而来,这是我昨晚的杰作。刚把包放下,
方姐就端着一个大碗过来了。满满一碗红烧肉,油光锃亮,还冒着热气。“趁热吃,
累一天了。”她把碗塞我手里。她的手指很暖,就是有点粗糙。“谢谢方姐。”“谢啥,
邻里邻居的。”她笑着摆摆手,“快吃吧,我回去了。”我端着碗,看着她关上门。真好。
我扒拉着碗里的肉,打开手机,想刷个短视频放松一下。一条本地新闻弹窗跳了出来。
“知名网红‘YOYO’家中遇害,警方已介入调查。
”配图是江畔公公馆拉起警戒线的照片。YOYO,于瑶。我脑子“嗡”的一下。
手里的碗没拿稳,“哐当”一声掉在地上。红烧肉和深色的汤汁溅了一地。那颜色,
让我想起了门缝里闻到的味道。还有她那句不耐烦的“快递放门口就行了”。
我最后一个见她的人?2警察找上门的时候,是第二天早上。我正蹲在地上收拾昨晚的残局,
门口就响起了敲门声。不是方姐那种温柔的两下,是又重又急的“梆梆”声。我打开门,
外面站着两个穿制服的男人。一个年纪大点,国字脸,眼神很利。一个年轻的,拿着个本子,
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怀疑。“陈实?”年长的那个开口,声音很沉。我点点头。
“我们是市局的,有点事想跟你了解一下情况。”我被带回了局里。审讯室的灯白得晃眼,
桌子是冰冷的铁。他们问了我一遍又一遍,昨晚的每一个细节。我把所有事情都说了。
从接到单子,到被保安拦下,再到把快递放在门口。当然,也包括那句从门缝里传出来的话。
“你说,你听到于瑶让你把东西放门口?”年轻警察抬起头,笔尖在本子上戳了戳。“对。
”“然后你就走了?”“对。”“你确定?”“我确定。
”年长的警察把一个平板电脑推到我面前。屏幕上正在播放一段监控录S像。
是江畔公馆于瑶家门口的走廊监控。视频里,我出现了。我按下门铃,等了一会儿,
然后推开了那扇虚掩的门,走了进去。过了大概五分钟,我才从里面出来,
把一个盒子放在门口,拍了张照,然后匆匆离开。我看着视频里的自己,手脚冰凉。
“这不是我。”我的声音在发抖。“视频里的人不是你?”年轻警察冷笑一声。“是我,
但我没进去!”我急了,“我发誓,我真的没进去!”“那视频怎么解释?”“我不知道!
这是假的!这是合成的!”年长的警察叹了口气。“陈实,我们查过了。于瑶的死亡时间,
就在你送快递的那个时间段。法医说,她是被人用一个钝器击中后脑死亡的。凶器还没找到。
”他顿了顿,看着我的眼睛。“而在她的指甲缝里,我们发现了皮屑组织。
经过DNA比对……”他没说下去,但我已经懂了。“是我的,对不对?
”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。他点了点头。“怎么可能?”我几乎要喊出来,
“我连她的手都没碰过!”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,我像个犯人一样被关着。
他们采集了我的指纹、血液、毛发。把我那辆破电驴也拖走了。我一遍遍地跟他们说,
我是被冤枉的,那个视频是假的。可没人信。证据太完美了。我唯一的希望,就是方姐。
她是我唯一的证人。我被放出来的时候,已经是第三天早上了。证据不足,暂时释放,
但不能离开本市,随传随到。我成了头号嫌疑犯。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安福里。楼道里,
几个邻居看到我,跟见了鬼一样,赶紧关上门。我走到三楼,看到方姐正站在我门口,
一脸焦急。看到我,她眼睛一亮,赶紧迎上来。“小陈!你可算回来了!
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?”她抓着我的胳膊,上下打量。那一刻,我鼻子一酸,
眼泪差点掉下来。这是三天来,第一个关心我的人。“方姐,我没事。”我声音沙哑。
“没事就好,没事就好。”她拍着我的背,“快进屋,我给你熬了粥。”她把我推进屋,
又跑回自己家,端来一锅热气腾腾的白粥,还有两碟小菜。“方姐,警察……有没有找你?
”我问。“找了。”她把粥盛好,递给我,“我跟他们说了,你那天晚上回来,
什么异常都没有,人也好好的。”“谢谢你,方姐。”“傻孩子,说什么谢。
”她坐在我对面,看着我,“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。肯定是搞错了。”我喝着粥,胃里暖了,
心里也暖了。也许事情没那么糟。只要方姐能给我作证,我就还有希望。吃完饭,
方姐帮我收拾了碗筷。“你好好休息,这几天肯定吓坏了。别怕,有姐在呢。”她走到门口,
又回头对我笑了笑。我点点头,看着她关上门。我瘫在沙发上,终于有了一丝困意。这几天,
我几乎没合眼。我闭上眼,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不知道睡了多久,
我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了。像是有人在哭。声音很轻,断断续续的,像个女人。我睁开眼,
屋里一片漆黑。哭声是从门外传来的。我坐起来,竖起耳朵听。那哭声,越听越耳熟。
很像……于瑶的声音。我给她送过几次快递,她说话就是那种有点尖,有点娇滴滴的调子。
我心头一紧。不会吧。都说人死后,有冤屈的,会头七还魂。今天是第几天了?我摸到手机,
屏幕亮光刺得我眼睛疼。第三天。我咽了口唾沫,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。从猫眼里,
我看到楼道的声控灯没亮,外面黑漆漆的。什么也看不见。但那哭声,就在我门外。
一声一声的,听得我头皮发麻。我不敢开门。我退回客厅,缩在沙发上,用被子蒙住头。
那哭声持续了大概半个多小时,才慢慢消失。我一夜没睡。3第二天,我顶着两个黑眼圈,
精神恍惚。昨晚的事,我跟自己说,是幻觉。压力太大了,都出现幻听了。对,一定是这样。
我强打起精神,准备出门买点吃的。刚打开门,就看见方姐提着一袋垃圾从楼上下来。
“小陈,醒了?脸色怎么这么差?”她关切地问。“没……没睡好。”我含糊地说。
“是不是因为案子的事?别想太多,清者自清。”她安慰道。“方姐,
你昨晚……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?”我还是没忍住问了。“声音?”她想了想,
“没有啊,我睡得沉。怎么了?”“没什么,可能是我听错了。”我没敢说实话。
说我听见死人的哭声,她不把我当神经病才怪。白天还好,阳光照进来,屋子里亮堂堂的,
心里的恐惧也散了不少。可一到晚上,那种不安感又回来了。我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,
电视声音开到最大。我想用光和声音,把那些不干净的东西赶走。十二点一过,
那哭声又响起来了。还是在门外。这一次,比昨晚更清晰。
我甚至能听到她在喊:“好疼……我死得好冤……”就是于瑶的声音。我捂住耳朵,
浑身发抖。这不是幻觉。是真的。她来找我了。因为我是最后一个见她的人,
所以她来找我申冤了?还是说……她觉得是我害了她,来找我索命了?我不敢待在客厅,
躲进了卫生间。我把门反锁,背靠着门板滑坐在地上。卫生间里没有窗户,
只有一盏昏黄的浴霸灯。我抱着膝盖,把头埋进去,不停地念叨“阿弥陀佛”。
我也不知道管不管用,反正电影里都这么演。哭声还在继续。
我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快跳出嗓子眼了。就在这时,我听见“滴答”一声。
像是水滴落在地上的声音。我抬起头。卫生间里没有漏水。“滴答。”又一声。
声音是从洗手台的方向传来的。我壮着胆子,扶着墙站起来,朝洗手台看去。
水龙头关得紧紧的。我的目光,落在了洗手台上方的镜子上。镜子里,
我的脸苍白得像一张纸。而在我的脸旁边,镜面上,有什么东西正在往下流。红色的。像血。
那些“血”,慢慢汇聚成了一个字。“死”。我“啊”的一声尖叫出来,腿一软,
瘫倒在地上。我手脚并用地往后退,直到后背撞上冰冷的墙壁。我死死地盯着镜子。
那个血红的“死”字,就在那里,触目惊心。外面的哭声停了。紧接着,响起了敲门声。
是我卫生间的门。“咚,咚,咚。”一下一下,敲在我的心上。“小陈?小陈你怎么了?
”是方姐的声音。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,连滚带爬地过去打开门。“方姐!鬼!有鬼!
”我指着镜子,话都说不囫囵。方姐冲了进来,顺着我指的方向看去。“哪有鬼?
”她一脸莫名其妙。我愣住了。我再回头看镜子。镜面干干净净,光洁如新。那个血字,
不见了。“刚才……刚才镜子上有个血写的‘死’字!”我急得快哭了。“你看错了。
”方姐走过去,用手摸了摸镜子,“这不好好的吗?你肯定是太紧张,眼花了。”她扶起我,
拍了拍我的背。“你看你,吓得一身冷汗。是不是又听到什么声音了?”我点点头。
“我就说你这两天不对劲。”她扶着我走出卫生间,“肯定是警察吓到你了,让你胡思乱想。
走,去姐家坐坐,姐给你倒杯热水压压惊。”我被她半拖半拽地带到她家。
她家和我家格局一样,但收拾得干净整洁。她给我倒了杯热水,让我坐在沙发上。“别怕,
啊,没什么鬼不鬼的。都是自己吓自己。”她坐在我旁边,语气温柔。我捧着热水杯,
手还是抖的。“可是……我真的听到了,也看到了。”“那就是巧合。”方姐说,“老房子,
管道多,有点声音不正常吗?镜子上的字,说不定是水汽凝结的,灯光一晃,你就看错了。
”她的解释很合理。但我心里还是觉得不对劲。那种恐惧,太真实了。
我们在她家坐了一会儿,我情绪慢慢稳定下来。“好了,回去睡觉吧。”方姐说,
“明天就没事了。”我点点头,站起身。“谢谢你,方姐。又麻烦你了。”“跟我客气什么。
”她送我到门口。我打开自己家的门,回头看了她一眼。她正靠在门框上,对我笑着。
那笑容,在昏暗的楼道灯光下,显得有点……奇怪。但我当时没多想,
只觉得她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对我好的人。我回到屋里,没敢再进卫生间。和衣躺在沙发上,
睁着眼睛直到天亮。我开始怀疑,我是不是真的疯了。4我决定去看心理医生。
不是因为信了方姐的话,而是我想确定自己到底疯了没。如果医生说我没病,
那就证明我经历的那些,都不是幻觉。我找了一家小诊所,医生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。
我把这几天的事都跟他说了。当然,我没提杀人案,只说我最近压力大,总出现幻听幻视。
他听完,推了推眼镜,给我开了一堆安神补脑的药。结论是:急性应激障碍。“年轻人,
别给自己太大压力。好好休息,按时吃药,过一阵子就好了。”我拿着药走出诊所,
心里更乱了。到底是我病了,还是这个房子有问题?接下来的两天,风平浪静。我按时吃药,
晚上再也没听到哭声,镜子上也没再出现血字。我开始相信,可能真的是我病了。案子的事,
警察也没再找我。我甚至开始幻想,也许他们找到了真凶,很快就能还我清白。
安福里有一只流浪橘猫,很胖,不怕人。方姐和我,还有楼下的几个老太太,都经常喂它。
它成了我们这栋楼的“公务员”。这天下午,我下楼扔垃圾,
看到那只橘猫正蹲在楼下的花坛边上。它没看我,而是仰着头,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们这栋楼。
具体来说,是盯着三楼的方向。也就是我和方姐住的那一层。我顺着它的目光看过去。
就是普通的墙壁,和两扇关着的窗户。没什么特别的。“咪咪,看什么呢?”我走过去,
想摸摸它。它被我吓了一跳,“喵”地一声,窜进了灌木丛里。我没在意,
扔了垃圾就上楼了。晚上,我躺在床上玩手机。那些安眠药效果不错,我很快就有了困意。
迷迷糊糊中,我好像听见了猫叫。很凄厉,就在窗外。我一个激灵,睡意全无。我爬起来,
走到窗边,拉开窗帘一条缝。窗外是老式居民楼的天井,对面就是邻居的墙壁。什么都没有。
猫叫声也停了。我松了口气,准备回去继续睡。就在我转身的一瞬间,
我的余光瞥到了对面的墙上。有一个黑影。很淡,一闪而过。像个人。我心脏猛地一缩,
赶紧又贴到窗户上看。墙上空空如也。又是幻觉?是药效过了吗?我回到床边,
把剩下的药片又吞了两颗。我只想好好睡一觉,什么都不要想,什么都不要看。第二天早上,
我被楼下一阵嘈杂声吵醒。我走到窗边,看到楼下的花坛边围了一圈人。方姐也在,
还有几个老太太。她们正对着花坛指指点点。我穿上衣服下了楼。“怎么了?”我问方姐。
方姐回过头,脸色很难看。“咪咪……死了。”我心里一沉,挤过去一看。那只胖橘猫,
躺在花坛里,身体已经僵硬了。脖子上有一道很深的勒痕。像是被人用绳子活活勒死的。
它的眼睛睁得大大的,直勾勾地看着三楼的方向。几个老太太都在那儿抹眼泪。“作孽啊!
谁这么狠心,对一只猫下这种手!”“就是啊,咪咪多乖啊,从来不挠人。
”我看着橘猫的尸体,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。我想起了昨天下午,它就是这样,仰着头,
看着三楼。它看到了什么?它是不是看到了那个飘在墙上的黑影?所以它才叫,
然后……被人灭口了?这个想法让我不寒而栗。我抬头,看向三楼。我的窗户,
和方姐家的窗户。那个黑影,到底是在哪家?5猫的死,像一根刺,扎在我心里。
警察来看了一眼,说是虐猫,查不到凶手,最后也就不了了之。但这事儿,让我彻底清醒了。
这不是幻觉,也不是闹鬼。是有人在装神弄鬼。目的,就是为了把我逼疯。我停了药。
我不想再被那些化学成分麻痹神经。我要清醒地看看,到底是谁在背后搞我。晚上,
我假装吃了药,早早就关了灯。我没有睡在床上,而是搬了把椅子,坐在了正对门的墙角。
那里是监控的死角,也是一个绝佳的观察位置。我手里握着一个空的啤酒瓶。如果有人进来,
我至少能反抗一下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。我的眼皮越来越沉。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,
我听到了声音。不是哭声,是钥匙的声音。有人在开我的门。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
我住的是老式防盗门,从里面反锁了,外面用钥匙是打不开的。
除非……他有能从外面打开反锁的工具。锁芯传来轻微的“咔哒”声。门,被推开了一条缝。
一个黑影,悄无声息地闪了进来。楼道里的光透进来,我看到那个人影很瘦,
穿着一身黑衣服,戴着帽子和口罩。他手里拿着一个东西,像个小喷壶。
他蹑手蹑脚地走到我床边,对着我的床喷了几下。一股淡淡的杏仁味传来。然后,
他退了出去,又轻轻地把门带上。整个过程,不超过一分钟。我坐在黑暗里,一动不敢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