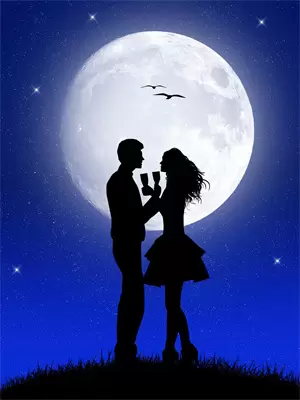1 告别乡村,重返故土1982年深秋的风,裹着北方特有的凉意,刮过红旗村的田埂。
林晓燕蹲在灶台前,最后一次帮李婶烧火,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,映得她眼里泛着水光。
“晓燕啊,这坛酱菜你带着,回城里要是实在难,就靠这手艺混口饭。
”老支书颤巍巍地递来一个粗瓷坛,坛口用红布扎得紧实,“还有这个,
你在村里种木耳的手艺好,这手册上记着新的菌种培育法,说不定能用上。
”林晓燕接过手册,指尖触到粗糙的纸页,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——她在这村里待了十年,
从十八岁的姑娘,熬到二十八岁的“老知青”,如今终于等到回城通知,可真要走了,
却满是不舍。村民们凑了钱,给她买了去城里的火车票。
李婶偷偷往她包里塞了袋晒干的木耳,压低声音说:“城里木耳贵,你留着自己吃,
要是能卖,也能换点钱。”火车哐当哐当地驶离小站,林晓燕望着窗外倒退的田野,
心里又期待又忐忑。她想起十年前,父母送她下乡时,母亲哭着说“一定要早点回来”,
如今终于要回来了,可城里的家,还会是她记忆里的样子吗?傍晚时分,火车到站。
林晓燕拎着大包小包,刚走出车站,就看到哥哥林晓强站在不远处,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,
脸上没什么表情。“哥。”林晓燕快步走过去。林晓强接过她手里的行李,
语气淡淡的:“家里住不下,你先去阁楼凑活,等以后有条件了再说。”林晓燕的心沉了沉,
却没说什么——她早料到,十年没回家,家里的情况不会太好。回到家,
狭窄的小平房挤得满满当当。嫂子王兰正坐在缝纫机前踩踏板,见林晓燕进来,头也没抬,
阴阳怪气地说:“哟,知青回来了?这十年在农村待着,没少受苦吧?不过话说回来,
你这回来,工作咋办啊?现在国营厂招人,都要城镇户口和介绍信,你哪有门路?
”林晓燕攥紧手里的酱菜坛,指尖泛白。父母坐在一旁,张了张嘴,最终却只是叹了口气。
晚饭时,桌上只有一盘炒白菜和几个窝窝头。王兰一边扒饭,一边说:“家里粮食紧张,
你回来,又得多张嘴吃饭……”“我自己能赚钱,不会给家里添麻烦。”林晓燕打断她,
语气坚定。王兰撇了撇嘴,没再说话。晚上,林晓燕躺在阁楼里,
狭窄的空间只能容下一张小床,屋顶还漏着风。她摸出老支书给的酱菜坛,打开坛口,
一股熟悉的酱香飘了出来。她想起在村里,村民们围着她一起做酱菜的日子,
心里渐渐有了底气——她有手艺,有双手,一定能在城里站稳脚跟。睡前,
她去供销社买牙膏,刚走到门口,就听到有人喊她:“林晓燕?”林晓燕回头一看,
是陈建军——他们是一起下乡的知青,陈建军三年前就回城了,听说进了国营机械厂当工人。
“建军哥,你怎么在这?”林晓燕又惊又喜。陈建军笑着说:“我家就在这附近,刚下班。
你刚回城?住在哪?”林晓燕把自己的情况简单说了说。
陈建军皱了皱眉:“阁楼条件太差了,你要是想摆摊做点小生意,缺个帮手,
我下班能来搭把手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他的地址和电话,
“有困难就找我。”林晓燕接过纸条,心里暖暖的。在这陌生的城市里,陈建军的话,
像一束光,照亮了她的路。2 阁楼创业,酱菜试水第二天一早,
林晓燕就去街道办打听工作。工作人员翻了翻她的档案,说:“知青回城找工作得排队,
现在名额紧张,你先回去等消息吧,有消息了我们会通知你。”林晓燕知道,
这“等消息”大概率是没下文了。她回到阁楼,看着角落里的酱菜坛,
心里有了主意——她可以摆摊卖酱菜,这是她在村里最拿手的活。说干就干。
她去菜市场买了辣椒、黄豆、萝卜干,又从供销社买了盐和糖。回到阁楼,
她把小煤炉搬出来,按照在村里学的方子,先把黄豆煮熟,
再和辣椒、萝卜干一起拌上盐和糖,装进坛子里密封。为了让酱菜更有特色,
她还泡了点木耳进去,提鲜增味。两天后,酱菜腌好了。林晓燕找了几个空玻璃瓶,
把酱菜装进去,贴上自己手画的标签,上面写着“晓燕农家酱菜”。
她推着哥哥不用的旧自行车,车后座绑着装满酱菜的篮子,去了菜市场。菜市场里人来人往,
热闹非凡,可她找了个角落站了半天,也没人过来问。旁边卖咸菜的张婶斜着眼睛看她,
语气带着嘲讽:“姑娘,你这农村来的酱菜,能干净吗?我这咸菜在菜市场卖了好几年,
老顾客都认我家的。”林晓燕没理她,继续守着摊位。直到快中午,
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走了过来,拿起一瓶酱菜闻了闻,说:“这酱菜的味儿,
有点像我当年在农村吃的大酱。”“奶奶,您尝尝,不好吃不要钱。
”林晓燕赶紧拿出一双干净的筷子,夹了一点酱菜递给老奶奶。老奶奶尝了一口,
眼睛一亮:“好吃!有嚼劲,还不齁咸。给我来两瓶。”有了第一单,后面就顺利多了。
路过的人见老奶奶买了,也纷纷过来尝,尝过之后,大多都买了一两瓶。一上午下来,
林晓燕卖了十瓶酱菜,赚了五块钱——这比国营厂学徒工一天的工资还多。傍晚收摊时,
陈建军骑着自行车过来了,手里还提着一个工具箱:“我听邻居说看到你在这摆摊,
就过来看看。你这小推车太旧了,我帮你修修,再加固一下,以后装更多东西也不怕。
”陈建军蹲在地上,拿出工具,熟练地修着小推车。夕阳照在他身上,
林晓燕看着他认真的样子,心里泛起一丝暖意。“建军哥,谢谢你。”林晓燕说。
陈建军抬起头,笑了笑:“谢什么,咱们是一起下乡的战友,互相帮忙是应该的。对了,
我帮你打听了,城郊有个批发市场,那里的玻璃瓶比供销社便宜一半,你下次可以去那进货。
”林晓燕记下批发市场的地址,心里暗暗感激——有陈建军的帮忙,她的创业路,
似乎顺畅了不少。接下来的几天,林晓燕每天都去菜市场摆摊,生意越来越好。
她还根据顾客的建议,调整了酱菜的口味,推出了微辣、特辣两种,满足不同人的需求。
可就在她以为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时候,麻烦却找上了门。3 同行打压,
另辟蹊径这天一早,林晓燕刚把摊位摆好,张婶就走了过来,手里端着一盆脏水,
故意往她的摊位前一泼,脏水溅到了酱菜瓶上。“你干什么?”林晓燕又气又急。
张婶双手叉腰,蛮横地说:“我干什么?这地方是我先占的,你一个农村来的知青,
凭什么抢我的生意?”她还对着路过的顾客喊:“大家别买她的酱菜!
我听说她的酱菜加了色素,吃了对身体不好!”顾客们一听,都停下了脚步,
原本想过来买酱菜的人,也纷纷转身离开。林晓燕的生意一落千丈,一整天下来,
只卖出去两瓶酱菜。收摊时,林晓燕坐在路边,心里又委屈又难过。她不明白,
自己靠手艺赚钱,没招谁没惹谁,为什么张婶要这么对她。就在她失落的时候,陈建军来了。
看到她闷闷不乐的样子,陈建军问清了缘由,安慰她说:“别难过,这种人不值得你生气。
咱们可以换个思路,不一定非要卖酱菜,你在村里不是种过木耳吗?城里木耳卖得贵,
而且很多人喜欢吃,你可以试试培育木耳。”陈建军的话提醒了林晓燕。
她想起老支书给她的木耳菌种手册,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——对啊,她在村里种过木耳,
有经验,而且木耳的销路应该比酱菜广。可培育木耳需要场地,阁楼太小,根本不够用。
陈建军看出了她的顾虑,说:“我有个朋友,在城郊有个废弃的仓库,现在没人用,
租金便宜,我帮你问问,能不能租给你。”第二天,
陈建军就带来了好消息——仓库租下来了,一个月只要二十块钱,还能接水接电。
林晓燕赶紧去买了锯末、麦麸,按照手册上的步骤,制作木耳培养基。
她把锯末和麦麸混合在一起,加水搅拌均匀,装进塑料袋里,然后接种菌种。每天,
她都要去仓库好几次,给培养基喷水,控制温度和湿度。陈建军下班后,也会来帮忙。
他帮林晓燕搭建了培育架,还找来一些旧木板,把仓库隔成了两个区域,一个用来培育木耳,
一个用来存放工具。两人一起搬材料、喷水、记录温度,累得满头大汗,却乐在其中。
半个月后的一天早上,林晓燕像往常一样去仓库查看,
突然发现培养基上长出了小小的木耳芽,黑色的,像一个个小耳朵。她激动得跳了起来,
赶紧给陈建军打电话。陈建军赶来后,看到木耳芽,也很高兴:“太好了!
咱们的努力没白费。等木耳长大了,就能卖钱了。”林晓燕给农村的老支书写了封信,
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。老支书很快就回信了,信里说:“村里的土地也适合种木耳,
要是你城里卖不出去,就拉回村里,咱们一起想办法。”看着老支书的信,
林晓燕心里暖暖的。她知道,无论她走到哪里,红旗村的乡亲们,都是她最坚实的后盾。
又过了半个月,木耳成熟了。林晓燕把木耳摘下来,晒干后装袋,拉去菜市场卖。
可让她没想到的是,城里人大多不认识干木耳,也不知道怎么做,看的人多,买的人少。
林晓燕有些着急,陈建军却安慰她说:“别着急,咱们可以去饭馆推销。
餐馆做炒菜、凉拌菜都需要木耳,用量大,肯定能卖出去。”于是,两人骑着自行车,
跑了一家又一家餐馆。大多数餐馆的老板都婉言拒绝了,直到他们来到一家小饭馆,
老板听他们介绍完木耳的好处,又看了看木耳的品质,说:“我先订五斤试试,
要是顾客反响好,我再跟你们订。”林晓燕和陈建军喜出望外,赶紧把木耳交给老板,
还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。几天后,餐馆老板给林晓燕打电话,说:“你们的木耳质量很好,
顾客都说好吃,我再订十斤,另外,我还介绍了几家餐馆给你们,他们也想订木耳。
”林晓燕拿着电话,激动得手都在抖——她的木耳,终于有销路了!4 木耳滞销,
亲情裂痕随着餐馆订单的增加,林晓燕的木耳生意渐渐有了起色。
她每天忙着采摘、晾晒、送货,虽然累,但心里很充实。可就在这时,新的问题出现了。
她从农村收购的一批木耳,因为天气潮湿,有些发霉了,没法卖给餐馆。
看着堆在仓库里的发霉木耳,林晓燕心疼得不行——这可是她花了不少钱收购来的。
更让她头疼的是,哥哥林晓强看到她堆在阁楼里的木耳,又开始冷嘲热讽:“我早就说过,
你这就是不务正业!好好找份稳定的工作不行,非要搞这些破玩意儿,现在好了,
木耳发霉了,钱也赔了!”林晓燕本来就心情不好,被哥哥这么一说,
忍不住反驳:“我搞这些怎么了?我靠自己的双手赚钱,没花家里一分钱!
”“你还好意思说?你住阁楼,用家里的水和电,不是花家里的钱是什么?
”林晓强也来了火气。嫂子王兰在一旁煽风点火:“就是!天天弄得家里一股木耳味,
难闻死了!我看你还是赶紧把这些木耳扔了,找份正经工作吧。”说着,
王兰就拿起阁楼里的一坛酱菜,扔到了门外。酱菜坛摔在地上,碎了一地,
酱香混着泥土的味道,弥漫在空气中。林晓燕看着碎掉的酱菜坛,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。
她冲进屋里,收拾好自己的东西,就往外走。“你去哪?”母亲急忙拉住她。“我去仓库住,
以后不麻烦你们了。”林晓燕甩开母亲的手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她在仓库里找了个角落,
铺了些干草,就当成了床。晚上,仓库里又冷又黑,她裹紧被子,心里满是委屈。就在这时,
门外传来了敲门声。“晓燕,是我。”是陈建军的声音。林晓燕打开门,
陈建军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,还有一床被子。“我听你妈说你搬到仓库来了,
就给你带了点吃的,还有一床被子,晚上冷,别冻着。”陈建军把保温桶递给她,
“里面是我妈做的红烧肉,你赶紧趁热吃。”林晓燕接过保温桶,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。
她一边吃着红烧肉,一边跟陈建军说起了家里的事。陈建军听后,
安慰她说:“别跟你哥和嫂子一般见识,他们也是担心你。等你生意做得更好,
他们就会理解你了。对了,发霉的木耳别扔,我有个朋友是做饲料加工的,
他说发霉的木耳可以用来做饲料,我帮你联系好了,他愿意按低价收购。”林晓燕没想到,
发霉的木耳还能卖钱,心里一下子轻松了不少。第二天,
陈建军就帮林晓燕把发霉的木耳卖给了饲料厂,虽然没赚多少钱,但也减少了不少损失。
林晓燕重新振作起来,她改进了木耳的储存方法,还跟农村的老支书商量,
让村民们在采摘木耳后,先晒干再寄给她,避免木耳发霉。渐渐地,
她的木耳生意越来越稳定,订单也越来越多。她赚了钱,给父母买了新衣服,
还寄了些钱给农村的老支书,感谢他的帮助。父母对她的态度好了很多,
母亲还经常去仓库看她,给她带些吃的。可哥哥林晓强,还是对她冷冰冰的,
总觉得她做的是“小打小闹”,成不了气候。林晓燕没在意哥哥的态度,她知道,
只要自己坚持下去,总有一天,会让哥哥刮目相看。这天,
她接到了一个大订单——一家大酒店要订一百斤木耳,用来做婚宴的菜品。林晓燕高兴坏了,
她赶紧联系农村的村民,让他们多采摘些木耳,尽快寄过来。可就在她准备送货的时候,
却发现仓库里的木耳不够了。她急得团团转,陈建军得知后,说:“别着急,
我帮你去外地的批发市场看看,说不定能买到木耳。”陈建军连夜去了外地,第二天一早,
就拉着一百斤木耳回来了。林晓燕顺利地把木耳送到了大酒店,拿到了货款。看着手里的钱,
林晓燕心里满是感激——要是没有陈建军的帮忙,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她看着陈建军,
认真地说:“建军哥,谢谢你。要是没有你,我真的走不到今天。”陈建军看着她,
笑了笑:“咱们是朋友,互相帮忙是应该的。以后,咱们一起努力,把生意做得更大。
”林晓燕点了点头,心里暗暗下定决心,一定要好好干,不辜负陈建军的帮助,
也不辜负自己的努力。5 合伙创业,注册招牌陈建军的话像一颗定心丸,
让林晓燕心里涌起一股热流。她看着仓库里整齐堆放的木耳和酱菜,
又看了看眼前眼神坚定的陈建军,深吸一口气说:“建军哥,我想跟你合伙干!你懂机械,
能帮我改进培育设备;我懂种养殖和销售,咱们俩一起,肯定能把生意做好!
”陈建军眼睛一亮,他早就有这个想法,只是怕林晓燕有顾虑,没好先开口。
“我也是这么想的!” 他激动地说,“我在工厂待够了,每天重复一样的活,没奔头。
跟你一起干,虽然累,但心里踏实,还有盼头!”第二天,陈建军就去工厂递交了辞职报告。
厂长挽留他:“你技术好,再过两年就能升车间主任,怎么说走就走?
” 陈建军笑着摇头:“谢谢您的看重,但我想跟着朋友一起创业,闯一闯。”辞职后,
两人凑了五百块钱,直奔工商局。1982 年的工商局办事大厅人不多,
工作人员接过他们的申请材料,看着 “晓燕农产品经营部” 的名字,
笑着说:“现在个体户越来越多,你们年轻人有闯劲,好好干!”拿到营业执照的那天,
林晓燕和陈建军特意去饭馆吃了顿饺子。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来,
陈建军夹起一个递给林晓燕:“来,庆祝咱们的经营部成立,以后咱们就是老板了!
” 林晓燕咬了一口饺子,心里又甜又暖 —— 这是她回城后,
第一次觉得自己真正在城里扎下了根。他们在菜市场附近租了个小门面,门面不大,
却收拾得干净整洁。墙上挂着营业执照,货架上摆着瓶装酱菜、袋装木耳,
还有从农村收购的黄花菜、香菇。开业那天,李婶托人从农村捎来一筐新鲜蔬菜,
老支书还写了封贺信,让他们心里满是感动。为了提高木耳产量,
陈建军把仓库里的木架子改成了铁制培育架,还从废品站淘来旧零件,
组装了一个简易温控设备。“这样一来,不管外面温度怎么变,
仓库里的温度都能保持在最适合木耳生长的范围。” 陈建军擦着汗说。林晓燕试了试设备,
果然比以前方便多了,木耳长得又快又好。一天,一家大餐馆的采购经理找到他们,
说要订一百斤木耳,但是要求先送货,一个月后再付款。林晓燕有些犹豫,
一百斤木耳可不是小数目,要是收不到钱,损失就大了。陈建军看出了她的顾虑,
拍了拍胸脯:“我去跟他们谈,咱们签个合同,把付款时间、金额都写清楚,有合同在,
不怕他们赖账。”陈建军带着合同去了餐馆,采购经理见他们做事正规,爽快地签了字。
一个月后,餐馆按时付了款,还跟他们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。林晓燕看着到账的钱,
对陈建军说:“建军哥,幸好有你,不然我真不敢接这个订单。”这天晚上,
林晓燕给老支书打了个长途电话,声音里满是兴奋:“老支书,我们的经营部开起来了,
生意还不错!村里要是种了木耳、黄花菜,尽管往我这送,我给的价格肯定比批发市场高!
” 电话那头的老支书笑得合不拢嘴:“好!好!我这就组织村民们种,
以后咱们村的农产品就不愁卖了!”挂了电话,林晓燕看着窗外的灯火,心里充满了希望。
她知道,她的创业路才刚刚开始,未来还有很多挑战,但只要和陈建军一起,
和村里的乡亲们一起,她有信心把这条路走得更远。6 资金短缺,
贵人相助经营部的生意越来越好,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。
可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—— 他们需要更多的钱采购原材料、扩建仓库,
可两人的积蓄早就花光了,手里的钱只够维持日常周转。“咱们去银行贷款吧。
” 林晓燕提议。第二天,他们就去了银行。信贷员接过他们的申请材料,
看了看说:“你们是个体户,没有固定资产抵押,不符合贷款条件,这贷款没法批。
”走出银行,两人都有些沮丧。陈建军叹了口气:“要是能有笔钱就好了,
咱们就能扩大规模,接更多订单。” 林晓燕也皱着眉,她想起仓库里堆着的订单,
心里急得不行。这天,他们去城郊批发市场采购玻璃瓶,刚走到一家粮油店门口,
就被店主叫住了。店主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叔,姓赵,大家都叫他赵老板。
“你们是卖酱菜和木耳的吧?” 赵老板笑着说,“我在超市见过你们的产品,
我老板说你们的酱菜味道特别好。”林晓燕愣了一下,随即笑着点头:“是啊,赵老板,
我们是晓燕农产品经营部的。” 赵老板热情地把他们请进店里,
倒了杯茶说:“我看你们的生意挺好,怎么愁眉苦脸的?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?
”林晓燕见赵老板人很和善,就把资金短缺的事跟他说了。赵老板听后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