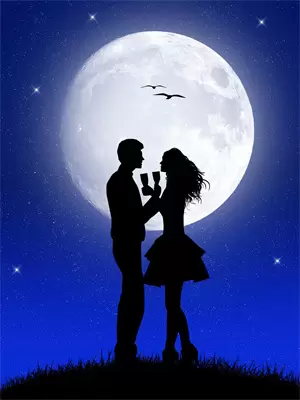林知夏在巷尾旧书店驻足时,七月的蝉鸣裹挟着热浪,把午后的时光烘得又黏又长。
书店门楣上挂着块褪色的木牌,“拾光书屋”四个字被岁月磨得模糊,推门时,
挂在门后的铜铃发出“叮铃”一声轻响,像是唤醒了沉睡的旧时光。
店内弥漫着旧书特有的油墨香,混着墙角除湿袋淡淡的潮气,
空气里还飘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檀香——后来她才知道,那是店主老太太用来防虫的。
书架从地面堆到天花板,泛黄的书页挤在一起,有的书脊上贴着手写的标签,字迹歪歪扭扭,
却透着股认真。林知夏的指尖在书架上轻轻划过,
掠过一本本封面磨损的小说、卷边的工具书,直到触到那本深褐色封皮的书时,
动作忽然顿住。那本书藏在书架最内侧,被几本厚词典压着,只露出小半截封皮。
林知夏伸手把它抽出来,指尖刚碰到封面,就觉出了不一样的质感——不是普通的硬壳纸,
倒像是某种粗布压制成的,表面磨出细密的毛边,摸起来像触着外婆织的老棉絮,
带着时光沉淀的温软。书脊上用烫金字体印着《季风观测手记》,字迹已经有些斑驳,
却仍能看出当年的精致。她捧着书走到窗边的木桌旁坐下,阳光透过蒙着薄尘的玻璃窗,
在书页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翻开扉页时,一张泛着黄的牛皮纸掉了出来,捡起来一看,
上面用蓝黑钢笔写着一行小字:“待季风过境,可往樟树下寻我”。字迹清隽,
笔锋带着点少年人的锐气,末尾缀着个比指甲盖还小的船锚印记,墨水洇在纸纤维里,
透着淡淡的纸香,像是把三年前的风都封在了里面。“姑娘是来寻书的?
”一个温和的声音从柜台后传来。林知夏抬头,看见个穿藏青斜襟布衫的老太太,
正从藤椅上慢慢起身。老太太戴着副玳瑁老花镜,镜片后的眼睛透着慈祥,
藤椅旁摆着个搪瓷杯,杯壁上印着“劳动最光荣”的红字,里面泡着半杯泛褐的菊花茶,
热气袅袅,把她的脸笼在一层薄雾里。“我随便看看,”林知夏把牛皮纸夹回扉页,举起书,
“您知道这本书的来历吗?”老太太走到桌边,接过书翻了两页,
指尖在扉页的船锚印记上轻轻摩挲,像是在触摸一段遥远的回忆。她摇着手里的竹骨蒲扇,
风里裹着旧书的油墨味:“这书搁在角落三年了,原主是个穿蓝衬衫的年轻人,眉清目秀的,
说话温温柔柔。他总来店里抄气象数据,每次都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,一坐就是一下午,
临走时还会帮我把散落的书摆好。”老太太顿了顿,呷了口菊花茶,
声音慢了下来:“他走的那天,也是个夏天,下着小雨。他背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,
把这本书放在柜台上,说要是以后有人带走它,就把夹在第73页的东西一并相赠。
我问他要去哪里,他说要跟着科考船走,去追太平洋上的季风,还说等季风回来的时候,
他就回来取这本书。”林知夏的心轻轻一动,指尖捻着书页,小心翼翼地往后翻。书页很薄,
纸面上能看见细小的纤维,翻到第73页时,一张泛黄的明信片轻轻滑落,掉在木桌上,
发出“嗒”的一声轻响。她弯腰捡起明信片,
正面印着望海镇的老码头——褪色的海浪拍打着木质栈道,几艘旧渔船泊在岸边,船帆收着,
像是累了的候鸟;远处的灯塔顶着红色的顶盖,在蓝灰色的天空下,像个沉默的守护者。
背面用铅笔细细画了棵枝繁叶茂的樟树,树干粗壮,枝桠向四周伸展,
遮住了大半个画面;树下的青石板被红笔圈出来,大小刚够两人并肩坐,
石板旁还画了朵小小的雏菊,笔尖的弧度里藏着细碎的温柔。角落同样钤着个船锚印记,
比扉页上的稍大些,线条更清晰,像是用圆规仔细描过。“这是望海镇的老码头,
”老太太凑过来看了眼明信片,语气里带着点怀念,“我年轻的时候去过一次,
那时候码头还热闹,渔民们早出晚归,码头上满是鱼腥味和笑声。现在啊,
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,只剩下几艘旧渔船,偶尔有人划着去近海捕鱼。”“那个年轻人,
叫什么名字?”林知夏捏着明信片的指尖微微发烫,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莫名的熟悉感。
“叫沈砚,”老太太说,“以前在望海镇的气象站工作,听说做得很认真,
每天天不亮就去海边观测,晚上还在灯下整理数据。后来科考队来招人,
他毫不犹豫就报名了,说想去看看更广阔的海,看看太平洋上的季风到底是什么样子。
”林知夏的心猛地一跳,像是有颗小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,泛起层层涟漪。
她忽然想起上周邮箱里的实习通知——半个月前,
她向沿海多个海洋气象观测站投递了实习申请,只有望海镇的观测站回复了她,
邮件里附着的通知书上,右下角的印章是个小小的船锚,当时她没在意,现在想来,
竟和明信片上的印记有几分相似。“望海镇的海洋气象观测站,还在吗?
”林知夏的声音带着点不易察觉的急切。“在呢,就在镇子边缘的小山坡上,
”老太太笑着点头,“听说现在还有人驻守,就是不知道忙不忙。姑娘,你对那地方感兴趣?
”林知夏把明信片夹回书里,指尖轻轻拂过封皮上的毛边,
像是做出了某个决定:“我申请了那里的实习,下周就要去报到。
”老太太眼里闪过一丝惊喜,随即又露出欣慰的神色:“那可真是缘分!说不定你到了那里,
还能遇见那个叫沈砚的年轻人呢。”那天离开书店时,林知夏把《季风观测手记》抱在怀里,
像是捧着件稀世珍宝。铜铃再次“叮铃”作响,老太太站在门口,挥着蒲扇跟她说:“姑娘,
要是见到沈砚,记得跟他说,他放在店里的书,终于有人带走了。”林知夏点头应下,
转身走进巷子里。午后的阳光依旧炽热,蝉鸣还在耳边聒噪,可她却觉得心里凉丝丝的,
像是揣着一阵来自望海镇的海风。收拾行李时,
林知夏把《季风观测手记》放在帆布包的最上层,
下面垫着块柔软的棉布——那是她小时候穿的连衣裙改的,浅蓝色的布料上印着小雏菊,
现在刚好用来保护这本旧书。她翻书时,夹在里面的明信片总爱滑出来,有次掉在地上,
她捡起来时,指尖不小心蹭到了背面的樟树画,铅笔屑沾在指腹上,细细的,
像是时光的碎屑。后来她索性把明信片夹在手机壳里,
这样低头就能看见那棵画得认真的樟树,看见树下的青石板,心里就会泛起一股莫名的期待。
出发去望海镇那天,天刚蒙蒙亮。火车站的人不多,广播里循环播放着检票通知,
声音透过嘈杂的人群,显得有些模糊。林知夏背着帆布包,手里攥着火车票,站在月台上,
看着远处的铁轨延伸向天际,心里既紧张又兴奋。火车启动时,
车轮与铁轨摩擦发出“哐当哐当”的声响,像是在为这场旅程伴奏。林知夏靠窗坐下,
把《季风观测手记》放在小桌板上,翻开扉页,盯着那行“待季风过境,
可往樟树下寻我”的字迹,不知不觉就出了神。她想起老太太说的话,
想起那个叫沈砚的年轻人,想起望海镇的老码头和灯塔,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填满了,
软软的,暖暖的。随着火车不断向海边靠近,
窗外的景色渐渐变了——原本的农田变成了滩涂,远处的天空越来越低,与海面连成一片。
空气里的咸腥味也越来越重,透过车窗缝钻进来,带着大海特有的清新。
林知夏把脸贴在玻璃上,看着窗外掠过的渔船、晒在岸边的渔网,还有远处隐约可见的灯塔,
心跳不由得加快了几分。火车到站时,正好是傍晚。望海镇的火车站很小,只有一个站台,
站台上铺着的水泥地有些开裂,缝隙里长着几株野草。林知夏背着帆布包走出车站,
抬头就看见远处的海面被夕阳染成了熔金,波光粼粼,像是撒了一把碎钻。海风吹在脸上,
带着淡淡的咸腥味,拂去了旅途的疲惫。她按照实习通知书上的地址,
找了辆三轮车去观测站。车夫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叔,皮肤晒得黝黑,
笑起来露出两排整齐的白牙。他一边蹬着车,
一边跟林知夏聊天:“姑娘是来观测站实习的吧?咱们这望海镇,别看地方小,
可是个好地方,海边的风景美,空气也好,就是冬天风大了点。”“大叔,
您知道观测站的沈砚吗?”林知夏忍不住问。车夫愣了一下,随即点头:“知道啊!
沈砚这小伙子,可是个好孩子,以前在观测站工作的时候,对人可热情了,
镇上的人都喜欢他。后来他跟着科考船走了,说是去追季风,都三年了,还没回来呢。
”林知夏心里微微一沉,却又很快燃起希望——说不定他很快就会回来了呢。
三轮车沿着海边的公路行驶,路边的路灯渐渐亮了起来,暖黄的灯光洒在海面上,
像是为大海系上了一条金色的丝带。远处的灯塔也亮了,一闪一闪的,
像是在向归来的船只招手。大约过了二十分钟,三轮车停在了一座红砖墙建筑前。“到了,
这就是观测站。”车夫指着建筑说。林知夏付了钱,背着帆布包走到门口。
观测站的大门是两扇铁门,上面刷着的绿漆有些剥落,门口挂着块褪色的木牌,
上面写着“望海镇海洋气象观测站”,字体是手写的,苍劲有力。大门没锁,
林知夏轻轻推开门走进去,院子里种着几棵梧桐树,树叶在海风中轻轻晃动,
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。院子尽头是一栋两层的小楼,楼下的窗户亮着灯。林知夏刚走到楼下,
就看见一个穿灰色衬衫的男人从屋里走出来。男人五十多岁,头发有些花白,皮肤晒得黝黑,
眼角堆着细密的皱纹,手里拿着个搪瓷杯,里面装着热水。“你就是林知夏吧?
”男人看见她,笑着走上前,“我是站长老郑,早就等着你来呢。”“郑站长您好,
我是林知夏。”林知夏连忙问好。老郑热情地接过她的帆布包,
领着她往楼上走:“楼上有间朝南的宿舍,采光好,视野也棒,从窗户就能看见大海。
楼下那棵大樟树可有年头了,以前沈砚总在树下看书,有时候能坐一下午,
说是樟树的树荫凉快,还能听见海声。”“沈砚?”林知夏心里一动,“您也认识他?
”“认识啊,这小伙子可是我看着长大的,”老郑笑着说,“他父亲以前是镇上的渔民,
后来在一场风暴里出事了,他就跟着奶奶长大。大学毕业后,
他主动申请回镇上的观测站工作,说是要保护镇上的渔民,不让他们再受风暴的伤害。
”说话间,两人已经走到了二楼的宿舍门口。老郑打开门,里面是一间不大的房间,
摆着一张单人床、一张书桌和一个衣柜,书桌上放着一盏台灯,窗台上还摆着一盆绿萝,
绿油油的,透着生机。林知夏走到窗边,推开窗户,海风立刻涌了进来,带着咸腥味,
吹在脸上很舒服。从窗户往下看,正好能看见楼下的大樟树——树干粗壮,需要两人合抱,
枝桠向四周伸展,遮住了大半个院子,树下果然有块青石板,边缘被磨得光滑,
和明信片上画的分毫不差。“怎么样,这房间还满意吧?”老郑站在门口问。“满意,
谢谢您,郑站长。”林知夏点点头,心里满是欢喜。老郑又跟她说了些观测站的注意事项,
比如每天要记录三次气象数据,分别在清晨、午后和深夜,遇上恶劣天气要及时上报,
还要协助维护观测设备等等。临走时,他拍了拍林知夏的肩膀:“别紧张,慢慢来,
有什么不懂的就问我。”老郑走后,林知夏把帆布包放在书桌上,
小心翼翼地把《季风观测手记》拿出来,放在台灯下。她翻开书,
再次看到扉页上的字迹和明信片,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——她想去看看那棵樟树,
看看树下的青石板。她抓起外套,快步跑下楼。院子里很安静,
只有海风吹动树叶的声音和远处的海浪声。林知夏走到樟树下,蹲下来,
指尖轻轻拂过青石板的表面,冰凉的触感透过指尖传来,带着岁月的痕迹。